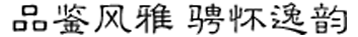古代朔州的诗歌创作,在一般的诗史中不太为人们所重视,似乎处在可有可无的地位,对它们的了解、研究也颇显不足。其实,从中华民族的发展来看,古人咏朔诗有着较为特殊的意义。它们既受唐宋诗歌的影响、滋养,同时也有唐宋诗所无法掩抑的精光异彩。它们既勃发着北方民族禀自塞外的浑莽之气,又展示着中华诗歌传统接受“源头活水”后的崭新风貌。尤其是边塞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朔州古代边塞诗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打着古代的旗号,反映现实生活中民族间的争战。出征的部队称为汉兵,军队将领称为汉将,边塞称为汉塞,就连天上的月亮也称为汉月。这里所说的汉,一方面是个民族概念,指的是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同时它又是一个历史概念,用以指代曾经昌盛一时的汉王朝,由于边塞诗存在复古倾向,许多作品显得古色古香,把人带回了古代世界。
曾任明陕西巡抚的山阴人郭登庸在《秋暮登高有怀》诗中写道: “南来勾注接云州,汉主提兵出塞陬。扣马数言前未悟,困兵七日实堪忧。阴山雪野凋征旆,广武城开释系囚。莫谓齐人争口舌,羊裘一见本良谋。”(《山阴县志·明》)这首诗是郭登庸晚年回乡后写的,但是,诗中的汉主刘邦、齐人刘敬和困兵七日等典故,代表了那个时期边塞诗经常采用的托古以纪事抒怀的表现形式。
明代郭显忠在《登朔州城楼》诗中写道:“耀武先登百雉城,望中沙漠与云平。请封初聚单于种,置宋犹余汉将营。广武雪消春水漫,居延烟静晚霞明。防胡岂恃金汤险,幕府胸藏数万兵。”(《朔州志》)
朔州边塞诗在提及周边少数民族时,也往往沿袭汉代的称谓,把交战对手称为匈奴、胡人,把少数民族首领称为单于、冒顿。其实,匈奴族在南北朝时期已经不复存在,匈奴首领的单于、左贤王等称号也没有被其他少数民族沿袭。尽管如此,边塞诗人却借用他们来指代现实生活中与之交往的少数民族及其首领,使自己的作品带有古代气息。
明代于谦的《塞上即景》诗写道:“目极烟沙草带霜,天寒气暮景苍茫。炕头炽炭烧黄鼠,马上弯弓射白狼。上将亲平西突厥,前军尽斩左贤王。边城无事烽尘静,坐听鸣茄送夕阳。”(《朔县志》)
乔岱的《过山阴有作》诗写道:“利簇穿雕角弓劲,宝刀画戟相晖映。才闻冒顿血污轮,又见单于组系颈。尘沙漠漠万里平,幕南已是天王庭。三军唱凯卷戈甲,阴霾尽扫寰区清。”等都表现得很突出。
朔州古代边塞诗的作者在表达自己的豪迈情怀时,武将以霍去病等汉代名将为榜样,文人则经常以班超、贾谊自况。
明嘉靖时的山西巡抚闵照的《初出雁门》诗中写道:“泥封天堑三关戍,日射山阴跨马初。怅望菑畲尽荆棘,伤心邑里半丘墟。论兵只许骠姚将,破虏空余霹雳车。贾谊有怀书不得,几回幽独苦踌躇。”(《山阴县志·明》)
明代文学家谢榛在《塞门游》诗中写道:“几年欲向塞门游,北渡桑干重旅愁。画角悲凉孤馆夜,黄榆摇落九边秋。壮心未掷班生笔,浪迹堪怜季子裘。回首江湖任鸥鸟,漫嗟花发滞云州。”(《山阴县志·明》)
两诗中的骠姚将即霍去病,班生即班超,除贾谊外,还有季子苏秦。由此可见,朔州古代边塞诗无论是出自文人之手,还是武将所作,他们都把古代的出塞豪杰和自己联系在一起,把现实和历史沟通,用古代边塞豪杰的功勋业绩来勉励或比喻自己,把当前的行动置于民族融合的历史潮流中加以审视。
古代文人在创作朔州边塞诗时仿佛返回了已经逝去的年代,产生重走前人之路的感觉,有时候他们又有超越前人的豪迈情怀,认为今人在边塞所建立的功业是古人无法比拟的。
《朔县志》收录李世民的《饮马长城窟》诗写道:“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翰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迥戌危烽火,层峦引高节。悠悠卷旆旌,饮马出长城。寒沙迷骑迹,朔吹断边声。胡尘清玉塞,羌笛韵金钲。绝漠干戈戢,车徒振原隰。都尉反龙堆,将军旋马邑。扬麾氛雾静,纪石功名立。荒裔一戎衣,灵台凯歌入。”全诗表现出李世民超越前人的英雄气概,是在边塞地区民族交往中产生的豪迈情怀。
古代边塞往往是荒凉的,许多历史遗址在岁月风雨的侵蚀下难免凋零残破。面对这些景物,咏朔的诗人不时有一种死寂和毁灭的感触,作品也充满悲凉萧杀之气。
明成化年间的山西佥事许锐在《前题和韵》中写道:“衰草茫茫触眼悲,悠悠长路马行疲。山连恒岳知天限,河转桑干见水涯。邑小那堪三岁歉,兵荒谁恤万民饥。我来一憩凄凉馆,濡泪挑灯和万诗。”(《大同府志》·明)
明山阴邑令刘以守的《山阴感俗偶成》写道:“边邑入平丘,孤城烟霭浮。尘沙埋落日,霜霰集先秋。岭峻寒逾厉,河崩冻恰流。廛市几家寂,村墟空垒愁。酒旗招土窟,荞粒荐精糇。味珍黄鼠馔,暖羡白羔裘。炽炭搜山石,煎盐渍卤沤。春残耕未动,秋半稼言收。赋急逃亡尽,风漓隐射幽。饥羸良可恻,剽悍更堪忧。祗叹凋疲极,宁期督责休。铅割同捋虎,刃游惭解牛。政成无足纪,尸素觉怀羞。” (《山阴县志·明》)
残缺荒凉、兵荒马乱、断墙危壁、孤城烽燧,都是民族融合的历史见证,甚至高山大川、白云落日,也都承载着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光荣与耻辱,辉煌与衰落。由此来看,古代咏朔诗人在抒发那种由毁坏凋零而引起的种种感触时,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将以往的历史画面在作品和心灵中再生。
朔州古代人民以家为主,由此养成了安土重迁的习性,即使那些在民族融合大潮中激流勇进、长期生活在边塞的文人,依然非常留恋故土。《右玉县志》里收入的王攸隆的《和前韵》诗写道:“仰止高山云际楼,诗囊酒磕共登游。人从天半凭探望,鸟向平芜作意投。沙草饱经塞外色,黄花长忆故园秋。何时得遂图南志,蓑笠扁舟乐自悠。”把留恋故土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读后感慨颇多。